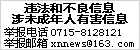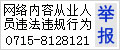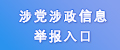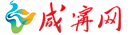 首頁 >> 專題報道 >> 2020專題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5周年 >> 正文
首頁 >> 專題報道 >> 2020專題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5周年 >> 正文雄踞長江三峽南岸一役扭轉(zhuǎn)抗戰(zhàn)局面 石牌硝煙遠浩氣永留存

掩映在現(xiàn)代建筑和樹木之間的碉堡

石牌保衛(wèi)戰(zhàn)中使用的機槍
楚天都市報記者 劉俊華 通訊員 李重慶 周娣
石牌,位于三峽大壩下游約20公里,是長江南岸的一個小村落,也是5A級景區(qū)三峽人家的一個渡口碼頭。
1943年5月至6月間,石牌保衛(wèi)戰(zhàn)在這里打響。這是一場關(guān)乎民族命運的戰(zhàn)役,也是抗戰(zhàn)的重大軍事轉(zhuǎn)折點,它以中國軍隊大勝告終,從而阻止了日軍沿長江西進重慶的企圖,對中國抗戰(zhàn)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9月1日,楚天都市報記者乘坐景區(qū)的游船,從江中眺望石牌,美景中殘留的碉堡、炮臺,仿佛在發(fā)出無聲的吶喊,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曾經(jīng)硝煙彌漫的過往。
硝煙散盡 要塞今建紀念館
前日,楚天都市報記者從宜昌沿長江西進,驅(qū)車約一個半小時,抵達三峽人家風景區(qū)。眼下正是旅游旺季,游客從各地蜂擁而至。
沿途的指示牌上,都有“石牌要塞”的標識。到了風景區(qū),記者才發(fā)現(xiàn),石牌原來位于長江對岸,需要乘坐景區(qū)的游船方可到達。
船至江心,能清楚看到長江至此拐了一個急彎。兩岸絕壁聳峙,有巨石如令牌立于岸邊,石牌由此得名。
恰逢上游三峽大壩泄洪,江水流勢湍急,讓人更增大江東去的感慨。
船上游人紛紛舉著手機、相機,拍攝沿岸風景,對上游的巴王寨、龍進溪等景點充滿期待。很少有人留意石牌——這個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要塞,在今天很容易被忽略。
登岸后,記者徑直向石牌村頭尋訪,在幾塊施工擋板和大樹的掩映中,發(fā)現(xiàn)幾座碉堡和炮臺,還有一座石牌抗戰(zhàn)紀念碑。應該就是這里了。
現(xiàn)場施工負責人告訴記者,這里正在建造石牌抗戰(zhàn)大遺址保護項目陳列館,預計年底竣工。
環(huán)顧四周,記者很難將這個寧靜的江邊小村與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聯(lián)系起來。但循著紀念碑后面的江岸探尋,水泥筑就的戰(zhàn)壕工事,像迷宮一樣分布在山嶺之間;一座廢棄的碉堡,混凝土墻足有50厘米厚,四周留有機槍射擊孔。
看來,戰(zhàn)爭留下的痕跡,并未完全被歲月沖刷掉。
小村印記 落后挨打教訓深
58歲的張元才,是土生土長的石牌人,他從小就聽老一輩人講當年的那場惡戰(zhàn)。他熱心地用摩托車載著記者,沿山路指點當年戰(zhàn)場的布局。
“我們這里其實是陳誠的指揮部。真正的一線戰(zhàn)場,在下游一點的平善壩,負責一線指揮的是十一師師長胡璉……”這個不善言辭的山里漢子,竟然對77年前的那場戰(zhàn)役如數(shù)家珍。
張元才帶著記者看了當年的戰(zhàn)地醫(yī)院,還有犧牲將士的忠烈祠。他說,當年村里幾十戶人家,家家都住著部隊,所以老一輩人,對戰(zhàn)役的情況非常清楚。
“都怪自己當時太落后了。中國軍隊守著這么有利的地形,卻因為武器和裝備不如日本人,戰(zhàn)斗才打得那么慘烈。好在我們的同胞用血肉之軀拼下來了,日本鬼子滅亡中國的野心被粉碎了。”張元才說。
57歲的陳兵在江邊經(jīng)營著一家小餐館。他的兒時記憶里,也真切地留著戰(zhàn)爭的痕跡。
那時還沒有葛洲壩和三峽大壩,江面寬度只有現(xiàn)在的三分之一。他家正好住在長江的拐彎處,門前500米長的江岸上,就殘留著5座炮樓,炮口全部對著長江下游來船的方向,就是為了阻擋日本人的軍艦上行。
后來,大江截流,江水上漲。陳兵的哥哥重新建房,新房就挨著其中一座炮樓的廢墟。
陳兵還記得,小時候長江枯水季,他和小伙伴經(jīng)常在江灘撿到日軍轟炸留下的炮彈殼。
“我們現(xiàn)在能笑著講這些往事,是因為我們國家強大了,不用擔心做亡國奴了。”陳兵說。對于今天的美好生活,他倍感珍惜。
老兵見證 保衛(wèi)家國灑熱血
71歲的簡興安,退休前是宜昌市夷陵區(qū)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潛心研究抗戰(zhàn)歷史多年。
他介紹,1938年10月,日軍侵占武漢,國民黨中央被迫遷都重慶,險峻的長江三峽成為“陪都”的天然屏障。石牌距宜昌城約20公里,自日軍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為拱衛(wèi)重慶的第一道門戶,戰(zhàn)略地位極為重要。
當時,從湖北到四川,還沒有一條可以走車的路,少有的羊腸小道也是險峻萬分,高山大嶺阻止了日軍西進的勢頭。進攻重慶必須打通長江,而打通長江必須占領(lǐng)石牌。就這樣,石牌這個當時不足百戶的小村,成為廣闊的中國戰(zhàn)區(qū)最關(guān)鍵的要塞。
石牌保衛(wèi)戰(zhàn)發(fā)生在1943年5月至6月間,是中國軍隊對日本軍隊以弱勝強、并最終以較小代價取得較大勝利的一次著名戰(zhàn)役,被西方軍事家譽為“東方的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
也有人懷疑石牌保衛(wèi)戰(zhàn)的戰(zhàn)略意義和慘烈程度。但簡興安多年走訪老兵獲得的史料證實,石牌確實是抗戰(zhàn)中關(guān)乎中華民族命運的“第一要塞”。
王正元,1924年出生于石牌附近的朱家坪村,參與石牌保衛(wèi)戰(zhàn)的國民黨一二一師當時就駐扎在這里。由于戰(zhàn)斗減員需要補充士兵,剛滿19歲的王正元被動員參了軍,成為一名工程兵。
2014年2月,90歲高齡的王正元在接受簡興安采訪時說:“戰(zhàn)斗怎么不慘烈呢?我都已經(jīng)結(jié)婚生子了,也要加入戰(zhàn)斗。當時好多指揮官,都是寫好了遺書上戰(zhàn)場的,守不住的話就要亡國了!”
忠魂永存 民族正氣蕩寰宇
記者采訪時看到,石牌抗戰(zhàn)紀念碑上,刻著一篇“陸軍第三十一師陣亡將士紀念塔志”。這篇志作于1945年,記錄著當年民族忠魂的浩然正氣。
“日寇侵擾,國都西遷,迨沙宜陷落,斯域以形勢險要,遂成國防要塞。至癸末春夏之交,湘鄂會戰(zhàn),寇旗迫進……石牌遂熠耀寰宇,一時有東方‘史達林格勒’之稱……”
當時負責防守石牌的國民黨第十八軍,共轄第十一、十八兩個師,其中十一師扼守要塞核心。上陣前,十一師師長胡璉舉行誓師大會,他和官兵們寫下遺囑,決心與石牌要塞共存亡。
戰(zhàn)區(qū)長官陳誠曾打電話問胡璉:“守住要塞有無把握?”胡璉回答:“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
2016年,記者采訪過胡璉的譯電室主任、抗戰(zhàn)老兵陶基烈。他說,他親眼見過胡璉寫給妻子的遺書:“我今奉命擔任石牌要塞守備,原屬本分,故我毫無牽掛。僅親老家貧,妻少子幼,鄉(xiāng)關(guān)萬里,孤寡無依,稍感戚戚,然亦無可奈何,只好付之命運……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歡樂。”
時隔70多年,陶老憶及當年的慷慨悲壯,仍感壯懷激烈。
如今,記者在石牌古鎮(zhèn)的江岸山嶺間穿行,炮火硝煙早已遠去。欣賞著江山如畫,感受著家國安寧,更覺民族忠魂長存人間。
編輯:但堂丹
上一篇:
下一篇:
棗宜會戰(zhàn)中張自忠力戰(zhàn)殉國 如今紀念館前緬懷人群不絕
相關(guān)新聞
-
家鄉(xiāng)那條母親河
孫芬(嘉魚)記憶中的家鄉(xiāng),不是一望無際的草原,而是放眼望去綠油油的麥田,還有大片黃色的油菜花海。生在魚鄉(xiāng),這個充滿著歷...
-
咸寧市十大標志性戰(zhàn)役指揮部辦公室工作簡報(2020年第13期)
2020年第13期(總第49期)咸寧市十大標志性戰(zhàn)役指揮部辦公室2020年7月16日我市圓滿完成長江沿岸造林綠化收官任務(wù)我市加強尾礦...
-
長江上的觀音閣:洪流難撼“閣堅強”

洪水中的觀音閣。陳凌志攝位于長江湖北鄂州城區(qū)段小東門外長江中的觀音閣,被稱為“萬里長江第一閣”近年來,一到汛期,這座...
-
守護母親河重現(xiàn)生機——多部門回應長江禁捕熱點問題
新華社記者于文靜、王優(yōu)玲近日,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切實做好長江流域禁捕有關(guān)工作的通知》,相關(guān)部門加快部署,確保2021...
-
新華網(wǎng)評:長江禁捕須善用“群防群治”
韓振最近,重慶江津區(qū)鴻鵠護魚志愿隊參與護魚行動的報道引發(fā)廣泛關(guān)注。動員群眾的力量,發(fā)揮“群防群治”優(yōu)勢,是做好長江流...
-
湖北長江干流全面禁捕拼圖完成
黃岡市政府7月3日發(fā)布公告,自2020年7月5日0時起,在長江黃岡段實行為期10年的全面禁捕。至此,長江干流流經(jīng)我省的8個市州已完...
-
湖北部署推進長江漢江禁捕和退捕漁民安置保障 王曉東要求壓實...
6月28日,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退捕漁民安置保障工作推進電視電話會議后,我省隨即召開會議對長江漢江禁捕退捕工作進行再動...
-
咸寧持續(xù)推進長江大保護十大標志性戰(zhàn)役 綜合排名居前列 七項...
鄂南咸寧, 128公里長江黃金水道依境東流。保護飲用水源地開出首張罰單近日,通城縣生態(tài)環(huán)境分局對在該縣北港鎮(zhèn)雁門水庫違法垂...
-
綠水青山“逼”出高質(zhì)量發(fā)展

截至3月26日8時,三峽水庫去冬今春已累計向下游補水達100億立方米,較去年同期多補水約5成,有效緩解了沿江各地春耕以及工業(yè)...
-
抗疫MV《愛在長江邊》——致敬英雄武漢

作詞:曙明(武漢鐵路局)他說:我在工作和生活當中,親眼看到了黨和政府的大愛,全國各地的馳援,還有武漢人民英勇頑強的精...
① 凡本網(wǎng)注明"來源:咸寧網(wǎng)"的所有作品,版權(quán)均屬于咸寧網(wǎng),未經(jīng)本網(wǎ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經(jīng)本網(wǎng)授權(quán)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quán)范圍內(nèi)使用,并注明"來源:咸寧網(wǎng)"。違反上述聲明者,本網(wǎng)將追究其相關(guān)法律責任。
② 凡本網(wǎng)注明"來源:xxx(非咸寧網(wǎng))"的作品,均轉(zhuǎn)載自其它媒體,轉(zhuǎn)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wǎng)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③ 如因作品內(nèi)容、版權(quán)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wǎng)聯(lián)系的,請在30日內(nèi)進行。

娛樂新聞
-
人藝“經(jīng)典保留劇目恢復計劃”開篇之作 《風雪夜歸人》4月25...
 2025-03-27
2025-03-27
-
摘下神探濾鏡 《黃雀》講述充滿“鍋氣”的人物和故事
 2025-03-27
2025-03-27